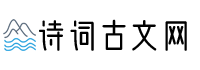
1. 关于悉尼的诗歌1、悉尼夏夜奏鸣曲 夏天的悉尼 海之旋律变奏鲜明 波涛的行程纷繁 崖岸却渴求宁静 浪花在沙滩飘洒长发 鸥鸟挑战泳者 歌剧院珠蚌吐出霞光 辉映海上熠熠银河 姗姗来迟的月夜 我仰卧海波微动的水面 带着随意的天真 编织异国浪漫的梦境 岸边的橡树林里 涌现一张朦胧笑脸 领我追随南澳燥热的风 漫游神奇的爱丽思泉 我知道 夏天最后的 玫瑰 跟现实梦幻无关 沙漠里无数飘忽的萤火 围绕我的灵魂争论不休 恍惚中突然雷声大作 一丝丝的雨水飘落 于是 在咸腥的泪雨里 我渐渐地苏醒 2、夜的悉尼港 摆脱了喧嚣与繁忙 那温柔的流水 无比宁静 月亮羞怯地笑了 拥抱大桥 舒展雪白的玉臂 雪梨的夜幷未睡去 街头靓男在追踪妖女 更有霓虹抛洒诱人的妩媚 从哪里飞来 贝多芬的琴音 花雨纷纷飘落水面 一朵浪花艶如一朵玫瑰 如水的月光 如梦的氛围 夜色使我迷失了方向 懵懵懂懂 踏入海浪掩没的归路 3、悉尼街头一瞥 黎明或暮色 沿着斑马线微笑 宁静的面孔 奔驰的车流 和平安详的乐章 停顿抑或演奏 褐色玻璃墙下 鸽子在啄食面包 白云在晴空遨游 邻近的海湾浪在喧闹 长发的男人 短发的女人 同样展示性感的肌肤 或黑得幽光 或白得发亮 旅游者与流浪汉 不同的步履 相同的行囊 太阳离开了地平线 影子里飘着惆怅。 2. 关于悉尼的诗歌1、悉尼夏夜奏鸣曲 夏天的悉尼 海之旋律变奏鲜明 波涛的行程纷繁 崖岸却渴求宁静 浪花在沙滩飘洒长发 鸥鸟挑战泳者 歌剧院珠蚌吐出霞光 辉映海上熠熠银河 姗姗来迟的月夜 我仰卧海波微动的水面 带着随意的天真 编织异国浪漫的梦境 岸边的橡树林里 涌现一张朦胧笑脸 领我追随南澳燥热的风 漫游神奇的爱丽思泉 我知道 夏天最后的 玫瑰 跟现实梦幻无关 沙漠里无数飘忽的萤火 围绕我的灵魂争论不休 恍惚中突然雷声大作 一丝丝的雨水飘落 于是 在咸腥的泪雨里 我渐渐地苏醒 2、夜的悉尼港 摆脱了喧嚣与繁忙 那温柔的流水 无比宁静 月亮羞怯地笑了 拥抱大桥 舒展雪白的玉臂 雪梨的夜幷未睡去 街头靓男在追踪妖女 更有霓虹抛洒诱人的妩媚 从哪里飞来 贝多芬的琴音 花雨纷纷飘落水面 一朵浪花艶如一朵玫瑰 如水的月光 如梦的氛围 夜色使我迷失了方向 懵懵懂懂 踏入海浪掩没的归路 3、悉尼街头一瞥 黎明或暮色 沿着斑马线微笑 宁静的面孔 奔驰的车流 和平安详的乐章 停顿抑或演奏 褐色玻璃墙下 鸽子在啄食面包 白云在晴空遨游 邻近的海湾浪在喧闹 长发的男人 短发的女人 同样展示性感的肌肤 或黑得幽光 或白得发亮 旅游者与流浪汉 不同的步履 相同的行囊 太阳离开了地平线 影子里飘着惆怅 3. 求赞美澳大利亚的诗歌,最好是英文版的,气势可以庞大些.轮 回 作者:[澳大利亚] 杰夫•古德费娄 译者:欧阳昱 五十年代 门悄悄打 开时 移民和难民 常被称为 “新澳大利亚人” 六十年代末 老澳大利亚人—— 才最后被纳入 人口普查数据 七十年代早期 白澳政策 正式解体 这是战后澳大利亚 远在后现代主义 和进口意大利羊毛西装之前 (这儿没有增值) 这时,雪山 水利工程雇的都是“勃格”,“倭格” 和“歹狗”① 日用漂白织物 工业 汽车 工业 制造 业 建筑 业 及大多数其他 跟手脚有关的工业也都一样(直到关税大行其道) 这些新澳大利亚人—— 他们可来劲呐 有些老 澳大利亚人也是的 尽管仍然 歧视黑人 袋鼠肉仍然 只喂宠物 丛林食物只留给 传教士吃 是的 这一切甚至都在谦卑的 黎巴嫩黄瓜 在澳大利亚落户之前 如今,在新千年 我的房东是希腊人 我的牙医是韩国人 我的咖啡店是意大利人的 我的蔬菜水果店是柬埔寨人的 我的超市是越南人的 我的小商品市场是德国人的 我的电脑专家是斯里兰卡人 我的法律顾问是希腊人 我的邻居是瑞典人 克罗地亚人、普鲁士人和英国人 我的侄儿侄女是 盎格鲁—意大利人 我的孙女是盎格鲁—印度人 我的电话簿一半都是 我几乎不会发音的名字 这是2001年,坦帕号船扬帆 进入历史 一个充满各种“倭格” “勃格”和“歹狗”的 国家 却害怕一船 “倭格” 所谓的“左”派和“右”派 政党—— 绕着 同心圆转圈子—— 他们的贪婪和他们的权力 吮吸着 这场漩涡的中心 ① 三者依次为bogs,wogs和dago,都是贬称,“勃格”指来自巴尔干半岛的移民,“倭格”指来自地中海及中东地区的移民,“歹狗”指意大利移民——译注。 轮 回 作者:[澳大利亚] 杰夫•古德费娄 译者:欧阳昱 五十年代 门悄悄打 开时 移民和难民 常被称为 “新澳大利亚人” 六十年代末 老澳大利亚人—— 才最后被纳入 人口普查数据 七十年代早期 白澳政策 正式解体 这是战后澳大利亚 远在后现代主义 和进口意大利羊毛西装之前 (这儿没有增值) 这时,雪山 水利工程雇的都是“勃格”,“倭格” 和“歹狗”① 日用漂白织物 工业 汽车 工业 制造 业 建筑 业 及大多数其他 跟手脚有关的工业也都一样(直到关税大行其道) 这些新澳大利亚人—— 他们可来劲呐 有些老 澳大利亚人也是的 尽管仍然 歧视黑人 袋鼠肉仍然 只喂宠物 丛林食物只留给 传教士吃 是的 这一切甚至都在谦卑的 黎巴嫩黄瓜 在澳大利亚落户之前 如今,在新千年 我的房东是希腊人 我的牙医是韩国人 我的咖啡店是意大利人的 我的蔬菜水果店是柬埔寨人的 我的超市是越南人的 我的小商品市场是德国人的 我的电脑专家是斯里兰卡人 我的法律顾问是希腊人 我的邻居是瑞典人 克罗地亚人、普鲁士人和英国人 我的侄儿侄女是 盎格鲁—意大利人 我的孙女是盎格鲁—印度人 我的电话簿一半都是 我几乎不会发音的名字 这是2001年,坦帕号船扬帆 进入历史 一个充满各种“倭格” “勃格”和“歹狗”的 国家 却害怕一船 “倭格” 所谓的“左”派和“右”派 政党—— 绕着 同心圆转圈子—— 他们的贪婪和他们的权力 吮吸着 这场漩涡的中心 杰夫•古德费娄(Geoff Goodfellow),诗人、教师,1949年生于阿德莱德,15岁辍学,当建筑工人二十年直至身体严重受伤,有“工人阶级诗人”之美誉。1983年以来出版九部诗集,如《等等》(1983),《半疯:发自旗语的声音》(1996),《**诗一发不可收拾》(1998)和《拳来拳去》(2004)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