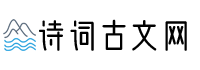
1.一首唐祈的诗,求原文唐祈(1920-1990),原名唐克蕃,出版的诗集有《诗第一册》(1948)、《唐祈诗选》(1990)。 旅行 游牧人 故事 十四行诗 严肃的时辰 女犯监狱 挖煤工人 老妓女 三弦琴 时间与旗旅行你,沙漠中的圣者,请停留一下分给我孤独的片刻。游牧人看啊,古代蒲昌海边的羌女,你从草原的哪个方向来?山坡上,你象一只纯白的羊呀,你象一朵顶清净的云彩。 游牧人爱草原,爱阳光,爱水,帐幕里你有先知一样遨游的智慧,美妙的笛孔里热情是流不尽的乳汁,月光下你比牝羊更爱温柔地睡。牧歌里你唱;青春的头发上很快会盖满了秋霜,不欢乐生活啊,人很早会夭亡哪儿是游牧人安身的地方?美丽的羌女唱得忧愁;官府的命令留下羊,驱逐人走。 1946故事湖水这样沉静,这样蓝,一朵洁白的花闪在秋光里很阴暗;早晨,一个少女来湖边叹气,十六岁的影子比红宝石美丽。青海省城有一个郡王,可怕的欲念,象他满腮浓黑的胡须,他是全城少女悲惨的命运;他的话语是难以改变的法律。 我看见他的兵丁像牛羊一样地豢养,抢掠了异域的珍宝跪在他座旁。游牧人被他封建的城堡关起来,他要什么,仿佛伸手到自己的口袋。 秋天,少女象忧郁的夜花投入湖底,人们幽幽地指着湖面不散的雾气。1940十四行诗——给沙合虽说是最亲切的人,一次离别,会划开两个人生;在微明的曙色里,想象不出更远的疏淡的黄昏。 虽然你的影子闪在记忆的湖面,一棵树下我寻找你的声音,你的形象幻作过一朵夕阳里的云;但云和树都向我宣告了异乡的陌生。别离,寓言里一次短暂的死亡;为什么时间,这茫茫的海水,不在眼前的都流得渐渐遗忘,直流到再相见的泪水里……愿远方彼此的静默和同在时一样,象故乡的树守着门前的池塘。 1945严肃的时辰我看见:许多男人,深夜里低声哭泣。许多温驯的女人,突然变成疯狂。 早晨,阴暗的垃圾堆旁,我将饿狗赶开,拾起新生的婴孩。沉思里:他们向我走来。 1946女犯监狱我关心那座灰色的监狱,死亡,鼓着盆大的腹,在暗屋里孕育。进来,一个女犯牵着自己的小孩:走过黑暗的甬道里跌入铁的栅栏,许多乌合前来的女犯们,突出阴暗的眼球,向你漠然险恶地注看——她们的脸,是怎样饥饿、狂暴,对着亡人突然嚎哭过,而现在连寂寞都没有。 墙角里你听见撕裂的呼喊:黑暗监狱的看守人也不能用鞭打制止的;可怜的女犯在流产,血泊中,世界是一个乞丐向你伸手,婴胎三个黑夜没有下来。啊!让罪恶象子宫一样割裂吧:为了我们哭泣着的这个世界!阴暗监狱的女烦们,没有一点别的声响,铁窗漏下几缕冰凉的月光;她们都在长久地注视死亡——还有比它更恐怖的地方。 1946挖煤工人比树木更高大的无数烟突,我看它们是怪癖的钢骨的黑树林。风和飞鸟都不敢贴近粗暴的烟囱,疯狂地喷吐出乌烟似的雾气,一团团乱云……比地面更卑下,比泥土阴湿,三百公尺的煤层,深藏着比牲畜还赤裸的夜一样污黑的一群男人;我们来自穷苦僻远的乡镇,矿穴里象小野兽匍匐爬行,惨绿的安全灯下一条条弯脊背在挖掘,黑暗才是无尽长的时刻,阳光摒弃了我们在世界之外,很快,生活只会剩下一副枯瘦的骨骼。 呵,呜嘟嘟的挖煤机、锅炉,日夜不停地吞吃着钟点,火车吐口气昂头驰向天边,它们的歌都哭丧似的吓人,当妻子小孩们每次注视险恶的升降机把我们扔下,穿过比黑色河床更深的地层,这里:没人相信,没人相信,地狱是在别处,或者很近。我们一千,一万,十万个生命的挖掘者,供养着三个五个大肚皮战争贩子,他们还要剥削不停——直到煤气浸得我们眼丝出血,到死,一张淡黄的草纸想盖住因愤怒而张开的嘴唇。 清算他们的日子该到了!听!地下已经有了火种,深沉的矿穴底层,铁锤将响起雷霆的声音……1946老妓女夜,在阴险地笑,有比白昼更惨白的都市浮肿的跳跃,叫嚣……夜使你盲目,太多欢乐的窗和屋,你走入闹市中央,走进更大的孤独。听,淫欲喧哗地从身上践踏:你——肉体的挥霍者啊,罪恶的黑夜,你笑得象一朵罂粟花。 无端的笑,无端的痛哭,生命在生活前匍匐,残酷的买卖,竟分成两种饥渴的世界。最后,抛你在市场以外,唉,那个衰斜的塔顶,一个老女人的象征深凹的窗:你绝望了的眼睛。 你塌陷的鼻孔腐烂城一个洞,却暴露了更多别人荒淫的语言,不幸的名字啊,你比他们庄严。1945三弦琴我是盲者的呼唤,引领他走向黑暗的夜如一个辽远无光的村落,微笑似的月光下没有一切支离残破,我只寻找那些属于不幸的奇幻的处所。 市街消失了白日的丑恶,路上的石头听我的歌声竖起它绊脚的耳朵,门扇后面的妇女来谛听命运,将来是一枚握得住的无花果吗!在哪里坠落?或者幸福如一束灿烂的花朵。但亡命的夜行人只能给我冷冷的一瞥,他不能向我诉说什么,只从我这里汲取些远了的故乡的音乐。 忽现的死亡隐退了,未知的疑虑,灾祸,在三根发亮的弦上是一片旷野。从他内心的黑暗听自我深长的喉管,震颤着祝福象一个人讲着饱经的忧患。 1948时间与旗一你听见钟响吗?光线中震荡的,黑暗中震荡的,时常萦回在这个空间前前后后它把白日带走,黑夜带走,不是形象的虚构,看,一片薄光中日和夜在交替。 2.一首唐祈的诗,求原文唐祈(1920-1990),原名唐克蕃,出版的诗集有《诗第一册》(1948)、《唐祈诗选》(1990)。 旅行 游牧人 故事 十四行诗 严肃的时辰 女犯监狱 挖煤工人 老妓女 三弦琴 时间与旗旅行你,沙漠中的圣者,请停留一下分给我孤独的片刻。游牧人看啊,古代蒲昌海边的羌女,你从草原的哪个方向来?山坡上,你象一只纯白的羊呀,你象一朵顶清净的云彩。 游牧人爱草原,爱阳光,爱水,帐幕里你有先知一样遨游的智慧,美妙的笛孔里热情是流不尽的乳汁,月光下你比牝羊更爱温柔地睡。牧歌里你唱;青春的头发上很快会盖满了秋霜,不欢乐生活啊,人很早会夭亡哪儿是游牧人安身的地方?美丽的羌女唱得忧愁;官府的命令留下羊,驱逐人走。 1946故事湖水这样沉静,这样蓝,一朵洁白的花闪在秋光里很阴暗;早晨,一个少女来湖边叹气,十六岁的影子比红宝石美丽。青海省城有一个郡王,可怕的欲念,象他满腮浓黑的胡须,他是全城少女悲惨的命运;他的话语是难以改变的法律。 我看见他的兵丁像牛羊一样地豢养,抢掠了异域的珍宝跪在他座旁。游牧人被他封建的城堡关起来,他要什么,仿佛伸手到自己的口袋。 秋天,少女象忧郁的夜花投入湖底,人们幽幽地指着湖面不散的雾气。1940十四行诗——给沙合虽说是最亲切的人,一次离别,会划开两个人生;在微明的曙色里,想象不出更远的疏淡的黄昏。 虽然你的影子闪在记忆的湖面,一棵树下我寻找你的声音,你的形象幻作过一朵夕阳里的云;但云和树都向我宣告了异乡的陌生。别离,寓言里一次短暂的死亡;为什么时间,这茫茫的海水,不在眼前的都流得渐渐遗忘,直流到再相见的泪水里……愿远方彼此的静默和同在时一样,象故乡的树守着门前的池塘。 1945严肃的时辰我看见:许多男人,深夜里低声哭泣。许多温驯的女人,突然变成疯狂。 早晨,阴暗的垃圾堆旁,我将饿狗赶开,拾起新生的婴孩。沉思里:他们向我走来。 1946女犯监狱我关心那座灰色的监狱,死亡,鼓着盆大的腹,在暗屋里孕育。进来,一个女犯牵着自己的小孩:走过黑暗的甬道里跌入铁的栅栏,许多乌合前来的女犯们,突出阴暗的眼球,向你漠然险恶地注看——她们的脸,是怎样饥饿、狂暴,对着亡人突然嚎哭过,而现在连寂寞都没有。 墙角里你听见撕裂的呼喊:黑暗监狱的看守人也不能用鞭打制止的;可怜的女犯在流产,血泊中,世界是一个乞丐向你伸手,婴胎三个黑夜没有下来。啊!让罪恶象子宫一样割裂吧:为了我们哭泣着的这个世界!阴暗监狱的女烦们,没有一点别的声响,铁窗漏下几缕冰凉的月光;她们都在长久地注视死亡——还有比它更恐怖的地方。 1946挖煤工人比树木更高大的无数烟突,我看它们是怪癖的钢骨的黑树林。风和飞鸟都不敢贴近粗暴的烟囱,疯狂地喷吐出乌烟似的雾气,一团团乱云……比地面更卑下,比泥土阴湿,三百公尺的煤层,深藏着比牲畜还赤裸的夜一样污黑的一群男人;我们来自穷苦僻远的乡镇,矿穴里象小野兽匍匐爬行,惨绿的安全灯下一条条弯脊背在挖掘,黑暗才是无尽长的时刻,阳光摒弃了我们在世界之外,很快,生活只会剩下一副枯瘦的骨骼。 呵,呜嘟嘟的挖煤机、锅炉,日夜不停地吞吃着钟点,火车吐口气昂头驰向天边,它们的歌都哭丧似的吓人,当妻子小孩们每次注视险恶的升降机把我们扔下,穿过比黑色河床更深的地层,这里:没人相信,没人相信,地狱是在别处,或者很近。我们一千,一万,十万个生命的挖掘者,供养着三个五个大肚皮战争贩子,他们还要剥削不停——直到煤气浸得我们眼丝出血,到死,一张淡黄的草纸想盖住因愤怒而张开的嘴唇。 清算他们的日子该到了!听!地下已经有了火种,深沉的矿穴底层,铁锤将响起雷霆的声音……1946老妓女夜,在阴险地笑,有比白昼更惨白的都市浮肿的跳跃,叫嚣……夜使你盲目,太多欢乐的窗和屋,你走入闹市中央,走进更大的孤独。听,淫欲喧哗地从身上践踏:你——肉体的挥霍者啊,罪恶的黑夜,你笑得象一朵罂粟花。 无端的笑,无端的痛哭,生命在生活前匍匐,残酷的买卖,竟分成两种饥渴的世界。最后,抛你在市场以外,唉,那个衰斜的塔顶,一个老女人的象征深凹的窗:你绝望了的眼睛。 你塌陷的鼻孔腐烂城一个洞,却暴露了更多别人荒淫的语言,不幸的名字啊,你比他们庄严。1945三弦琴我是盲者的呼唤,引领他走向黑暗的夜如一个辽远无光的村落,微笑似的月光下没有一切支离残破,我只寻找那些属于不幸的奇幻的处所。 市街消失了白日的丑恶,路上的石头听我的歌声竖起它绊脚的耳朵,门扇后面的妇女来谛听命运,将来是一枚握得住的无花果吗!在哪里坠落?或者幸福如一束灿烂的花朵。但亡命的夜行人只能给我冷冷的一瞥,他不能向我诉说什么,只从我这里汲取些远了的故乡的音乐。 忽现的死亡隐退了,未知的疑虑,灾祸,在三根发亮的弦上是一片旷野。从他内心的黑暗听自我深长的喉管,震颤着祝福象一个人讲着饱经的忧患。 1948时间与旗一你听见钟响吗?光线中震荡的,黑暗中震荡的,时常萦回在这个空间前前后后它把白日带走,黑夜带走,不是形象的虚构,看,一片薄光中日和。 3.普希金,汪国真的诗歌各一首,我就要两首普希金诗《我爱你》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我曾默默无语、毫无指望的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外国人的诗即使写得再好,翻译过来就不美了,普希金写得最美的是诗体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叙事长诗)《欧根-奥涅金》戈宝全译本。 提到汪国真的诗,我很悲愤和很无奈,严格的说汪国真写的不是诗,甚或可以说他根本就不会写诗,他写的东西东一鎯头、西一棒槌,使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只能骗骗不懂诗的无知的少男少女,可惜由于教育问题现在懂诗的人实在太少了,你读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吗?那才是诗。我国近百年来现代诗写得较好的人有:徐志摩 闻一多 李金发 穆木天 冯至 林徽因 戴望舒 李广田 艾青 卞之琳 何其芳 王佐良 穆旦 屠岸 周梦蝶 余光中 洛夫 贺敬之 周伦佑 王小妮 海子 安琪 辛笛 闻捷 陈敬容 罗寄一 郑敏 唐祈 袁可嘉 牛汉 羊令野 方思 罗门 昌耀 林泠 郑懋予 任洪渊 杨沫 叶维康 食指 江河 北岛 芒克 席慕容…… 附:汪国真的《致友人》不站起来 才不会倒下 更何况 我们要浪迹天涯 跌倒是一次纪念 纪念是一朵温馨的花。(汪国真的诗就是脑残人在说废话) 4.有一首诗里面有叶静的穆旦《春》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 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 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蛊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1942,2 【解析】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九叶”诗派代表性诗人,诗歌翻译家。在长期的艰砺而不无惨烈的生存背景下,诗人创设出属于自己良知的诗歌话语。 然而可悲的是,他优异的不可替代的诗歌写作却长期被忽略和悬置。 穆旦写作《春》这首诗时,时年24岁,正是青春情感和酷烈生命急需喷薄和释放的年龄。 诗在震荡中完成,在紧张中展开青春的阵痛和生命个体在与自然相遇中的感怀和情感抒写。那巨大的令人眩晕的内心深处的风暴,感染和撼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诗人的这首青年时期的诗作避开了一般诗人在青春期的情感无限泛滥、空前膨胀的滥情易感的危险(如郭沫若早期的火山喷发般的青春诗作)。应该说,这是一首节制的,矛盾的,悖论的,知性与直觉相融合的诗。 同是“九叶”诗派的诗人唐祈曾这样评价穆旦的诗——“他不仅纯熟地运用现代派技巧和表现手法,并且把艾略特的玄学的思维和奥登的心理探索结合了起来。”(《现代派杰出的诗人穆旦》,《诗刊》1987,2) 在《春》这首诗中,诗人关注的并不是外在的春天蓬勃滋长的自有事物,诗人更多地是倾心和专注于自己的直觉和知性,当然这种直觉是和知性的思辨紧密结合的,也即思维智性的直觉化。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另一位诗人狄兰·托马斯的诗句“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春草的蓬勃滋长被诗人视为是摇曳的绿色火焰,植物和火焰的内在的顽健的生命膂力从而在一个向度上彼此照亮,获得同一的内蕴。 开头这四句诗为我们展开了一个特异的生命图景。春草和植物的生长勃发过程被超强度凝缩在瞬间完成,那咝咝作响的向上昂扬的姿态正如燃烧的震颤的火焰。 这似乎也暗示了诗人内心深处的紧张和无奈——任何生命个体的过程都注定是短暂的,也许它曾经那么年轻富含旺盛的生命力。 春天,这生命奔跑的狂欢季节。 自然事物的释放的渴求,欲望的喷薄和生命的招摇,都是诗人的主观感性和青春身体的本体意义上的深层表达和凸现。 “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 那一只只在严寒的风中雪飘荡的植物终于迎来了暖春的第一抹朝阳。那风中刚刚苏醒摇晃的绿色的手掌,使人们很少意识到那种刚刚结束的“反抗”和“分娩”的艰砺过程和惨淡的履历。 当冬天僵硬板结的土地开始被小草拨开缝隙,并“伸出”绿色的生机和反抗的时候,春天真的到来了。可以想见,这不是单纯绝对客观的草木自然生成的春天,这不是机器摄下的呆板画面。 这是人的本体存在和青春肉体以及澎湃激情燃烧的苏醒的春天,生命的春天,燃烧的春天,欲望的春天,人类的春天。这是自然万有之下的生命的精神和智性光辉的本质表达和迹写。 “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如果你是醒了”这简单的一句其内涵是相当繁复的。 你——生命个体——的苏醒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和兴奋的事情。可是“如果”一词的假设和限制就蕴涵了另一个向度的内涵——有些人永远只是沉睡,精神和灵魂的沉睡。 多么可怕!在这两行诗句中,“欲望”和语境构成张力关系,紧张但又和谐。“欲望”一词是极为抽象的,而观看的主体“你”又是极其具体实在的。 其实,“满园的欲望”正是对以上四句的再次印证和夸赞。大地上疯长的激情和旺盛的生命正是“欲望”所点燃的“欢乐”。 意象“窗子”更应该是欲望和灵魂在岁月尘封中终于打开的窗户,它使生命的存在在广阔的空间舒展,张扬,远望。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蛊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紧闭的肉体,/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你们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 外界自然外物的生长和生命的敞开和“我们”年轻生命“紧闭的肉体”构成和弦的对话结构和矛盾的场阈。骚动不宁、欲望蓬勃的春天使为“永远的谜蛊惑”的生命内部的矛盾纠结更为剧烈。 自然的春天和人类个体的青春构成如此强烈的反差和纠缠不已的尴尬情境。连弱小的花朵都在抗争,发泄欲望,而人呢?所谓的万物的灵长呢?生命在催生的时刻却要“紧闭”欲望,就像泥土做成的鸟,那翅膀怎能飞翔?那歌声如何表达?无望的生命徒有冲动而难以“快乐”只能是宿命般的“无处归依”。 但是诗人并非无望的宿命般的苦闷。“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在彷徨、苦闷、压抑的无望之地,诗人是要“痛苦”地“等待”,等待真正生命喷薄的春天,这正是坚忍不拔的顽健的不懈抗争,是另一个意义层次上的生长的春天。这也是此诗的深层意蕴所在。 春天燃烧着催发着生命。诗人的青春体验在时间的淬炼中紧张的展开,一切都注定。 5.名词解释:归来者的诗1980年,艾青把他的一本诗集定名为《归来的歌》,与此同时,流沙河、梁南也写了题为《归来》和《归来的时刻》的诗。 “归来”,在这个期间,是一种诗人现象,也是一个普遍性的诗歌主题。这里称为“归来”(或“复出”)的诗人的,主要有这样几部分:50年代反右派运动中的右派诗人,如艾青、公木、吕剑、苏金伞、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昌耀、周良沛、孙静轩、高平、胡昭、梁南、林希等;在1955年“胡风集团”事件中罹难者,如牛汉、绿原、曾卓、冀汸、鲁藜、彭燕郊、罗洛、胡征等;因与政治有关的艺术观念,在50年代陆续从诗界“消失”的诗人,如辛笛、陈敬容、郑敏、唐湜、唐祈、杜运燮、穆旦、蔡其矫等(注:穆旦1994年2月参加抗日的中国远征军,先在杜聿明的司令部任随军翻译,后到207师,并随军赴缅甸战场,亲历了野人山的战役。1958年底,宣布他为“历史反革命”,“接受机关管制”,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见《穆旦诗全集》中的“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其实,穆旦在1977年2月去世,并未参与“归来”主题的写作。“九叶”诗派中的唐祈和唐湜,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 6.说说“中国新诗”派的诗歌主张及其对当代诗歌的影响.中国新诗派就是九叶派。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 九叶派"则是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的另一风格趋向的诗人群(又称"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另有专门介绍),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等.80年代出版有他们9人的诗歌合集《九叶集》,"九叶派"由此得名.文学史通常认为"九叶诗派"的艺术探求很有价值,拥有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诗人诗作,对新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诗学观念都有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