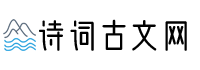
1.鉴赏《诗经·邶风·柏舟》赏析《诗经·国风·邶风·柏舟》有关诗经的评论文章和专著,不消说,肯定早已是汗牛充栋了。 但周汝昌说:“不要怕别人做过了,我们就没有事情做。”更何况,诗经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人不轻狂枉少年,正因为如此,我才有胆量来谈谈《诗经·国风·邶风·柏舟》。研究诗经,离不开烦琐的训诂考证,但我不具备这样的水平和能力。 我仅仅是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从已有的文本出发,不拘泥于具体的故事情节和历史背景,对《柏舟》作出自己的理解。我认为,只有这样,诗经才能突破训诂索隐带来的条条框框,外延它的表达范围,从而在新时代获得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生命。 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我心匪鉴,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诗经·国风·邶风·二子乘舟》有“二子乘舟,泛泛其景。” 古人乘船用“泛”字,给人一种舒缓貌,很能引起不尽的遐思。我读到此句的时候,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对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泛着小舟,在夕阳下,于荷花深处,谈情说爱,海誓山盟。 但如果结合全诗,我们发现,此处只是一个人在“泛”舟。此时,“泛”字的舒缓貌所流露出的不再是情意绵绵,而变成了精神恍惚。 我仿佛看到,徐徐前行着的小舟上正坐着一位心不在焉的诗人。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诗人是在发愁吗?如果是的,诗人又为何发愁呢?我又想到了《越女歌》:“今夕何夕兮,藆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誓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同样是乘舟,《柏舟》表达的是不是同样的情思主题呢?我借助于其他作品来揣摩这两句的含义,其实主要是受了中国传统的象征体系的影响。 这种象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诗经开始建立起来的,今天我们重读诗经,正可以把这种象征体系反过来运用,由后人的作品来体味最原始的诗经的象征系统。以上对诗人形象的种种猜测,仅仅是由“泛彼柏舟,亦泛其流”一句发散开去,我正是带着这些疑问迫不及待地读下去的。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此句交代了诗人确有“隐忧”,证实了我刚才的猜测。 “耿耿”二字的含义正可以由“耿耿于怀”来类推,“耿耿于怀”这个成语是不是由此而来呢?这个我们不妨存疑,也并不影响我们的阅读和理解。“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诗人说他(她)不是不能携酒以游。先秦时代,生产力低下,只有贵族才有可能喝酒,此句暗中交代了诗人的身份。 携酒以游,这似乎是男人的事,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就认定诗人是男子。这是因为贵族女子未必不会饮酒,后世女词人李清照不就是贵族女性饮酒的代表吗?所以诗人的性别问题还要存疑,还需要继续读下去。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这句话是说:镜子可以不分美丑善恶将一切东西的影象都照进去,我的心则不能像镜子那样不分美丑善恶都加以容纳。 这样的比喻令人耳目一新。我们一般地将镜子比喻成美好的事物,比如说“心如明镜”“以铜为鉴”等等。 我们正可以从这样的比喻中受到启发,有意识地运用这样的比喻,进一步扩大镜子在现代汉语中的象征意向。在内容上,此句表达了作者明辨是非的性格特点。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这两句话让我想到了《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刘兰芝“逼迫兼兄弟”,诗人的形象是不是和刘兰芝类似呢?通观《柏舟》的前两节,似乎说得通,诗人由此也很可能是一位女性。 但我们不能由此就敲定诗人和刘兰芝是同样的遭遇。凡此种种猜测,我们只有继续往下读,以求答案。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这两句比喻确实精彩,但不能给我以新鲜感,原因是《孔雀东南飞》中有如出一辙的句子:“盘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 但毫无疑问,《孔雀东南飞》明显化用了《柏舟》中的这两句。读古文的时候,我们总有类似的发现,就是一个诗人的诗句其实是化用了前人的诗句,有时候这个前人还是化用了比他更早的人的诗句。 这也是学习古代文学,对作品追根溯源的乐趣之一,特别是读诗经,这样的发现并不新鲜。这两句话用比喻的形式,进一步申明了诗人的抗争。 “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此句明确表示了诗人的威武不能屈。 “威仪棣棣”这样的形容似乎只适合男性,这让我对之前的认为诗人是女子的猜测产生了怀疑。但我也不能肯定“威仪棣棣”就不能形容女子,也许古代描述男女的词语与现代的词语不尽相同。 这其中就存在一些训诂的学问了。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这里的“群小”是谁呢?是“兄弟”?我们不得而知。 “觏闵既多,受侮不少。”诗人的命运似乎和刘兰芝差不多。 “静言思之,寤辟有摽。”《诗经。 2.什么是《诗经》的“正变说”正变说指的是风雅正变,也叫变风变雅。原出自《诗大序(毛诗序)》。 正变说内容:“正”、“变”的划分,不是以时间为界,而是以“政教得失”来分的。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 按照传统的观点,风、雅是指《诗经》的体裁,正、变是针对诗篇的内容而言的。然而关于风雅正变说的起源、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其存在的可能性,历代各家各派的学者却众说纷纭。 扩展资料: 传统的风雅是周王朝及管辖地区及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礼乐制度下的“正风正雅”最初并不是直接用以约束人的行为道德规范的,而是特定宴饮程序和意识下严格按照礼乐要求和规范进行的“娱神工具”。 在周代奴隶制社会下,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在各自的等级地位上安守本分,维持更高统治者“神”的威仪。 但在周王的暴虐统治下,《诗经》不再是被供奉在宗庙里娱神的酬酢有度的和美歌唱了,国家的动乱使得传统风雅中对现实的热情讴歌的理想状态被打破了。体现在《诗经》里的,便是“正风正雅”向“变风变雅”的转变。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变风变雅 3.鉴赏《诗经·邶风·柏舟》赏析《诗经·国风·邶风·柏舟》有关诗经的评论文章和专著,不消说,肯定早已是汗牛充栋了。 但周汝昌说:“不要怕别人做过了,我们就没有事情做。”更何况,诗经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人不轻狂枉少年,正因为如此,我才有胆量来谈谈《诗经·国风·邶风·柏舟》。研究诗经,离不开烦琐的训诂考证,但我不具备这样的水平和能力。 我仅仅是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从已有的文本出发,不拘泥于具体的故事情节和历史背景,对《柏舟》作出自己的理解。我认为,只有这样,诗经才能突破训诂索隐带来的条条框框,外延它的表达范围,从而在新时代获得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生命。 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我心匪鉴,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诗经·国风·邶风·二子乘舟》有“二子乘舟,泛泛其景。” 古人乘船用“泛”字,给人一种舒缓貌,很能引起不尽的遐思。我读到此句的时候,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对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泛着小舟,在夕阳下,于荷花深处,谈情说爱,海誓山盟。 但如果结合全诗,我们发现,此处只是一个人在“泛”舟。此时,“泛”字的舒缓貌所流露出的不再是情意绵绵,而变成了精神恍惚。 我仿佛看到,徐徐前行着的小舟上正坐着一位心不在焉的诗人。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诗人是在发愁吗?如果是的,诗人又为何发愁呢?我又想到了《越女歌》:“今夕何夕兮,藆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誓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同样是乘舟,《柏舟》表达的是不是同样的情思主题呢?我借助于其他作品来揣摩这两句的含义,其实主要是受了中国传统的象征体系的影响。 这种象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诗经开始建立起来的,今天我们重读诗经,正可以把这种象征体系反过来运用,由后人的作品来体味最原始的诗经的象征系统。以上对诗人形象的种种猜测,仅仅是由“泛彼柏舟,亦泛其流”一句发散开去,我正是带着这些疑问迫不及待地读下去的。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此句交代了诗人确有“隐忧”,证实了我刚才的猜测。 “耿耿”二字的含义正可以由“耿耿于怀”来类推,“耿耿于怀”这个成语是不是由此而来呢?这个我们不妨存疑,也并不影响我们的阅读和理解。“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诗人说他(她)不是不能携酒以游。先秦时代,生产力低下,只有贵族才有可能喝酒,此句暗中交代了诗人的身份。 携酒以游,这似乎是男人的事,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就认定诗人是男子。这是因为贵族女子未必不会饮酒,后世女词人李清照不就是贵族女性饮酒的代表吗?所以诗人的性别问题还要存疑,还需要继续读下去。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这句话是说:镜子可以不分美丑善恶将一切东西的影象都照进去,我的心则不能像镜子那样不分美丑善恶都加以容纳。 这样的比喻令人耳目一新。我们一般地将镜子比喻成美好的事物,比如说“心如明镜”“以铜为鉴”等等。 我们正可以从这样的比喻中受到启发,有意识地运用这样的比喻,进一步扩大镜子在现代汉语中的象征意向。在内容上,此句表达了作者明辨是非的性格特点。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这两句话让我想到了《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刘兰芝“逼迫兼兄弟”,诗人的形象是不是和刘兰芝类似呢?通观《柏舟》的前两节,似乎说得通,诗人由此也很可能是一位女性。 但我们不能由此就敲定诗人和刘兰芝是同样的遭遇。凡此种种猜测,我们只有继续往下读,以求答案。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这两句比喻确实精彩,但不能给我以新鲜感,原因是《孔雀东南飞》中有如出一辙的句子:“盘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 但毫无疑问,《孔雀东南飞》明显化用了《柏舟》中的这两句。读古文的时候,我们总有类似的发现,就是一个诗人的诗句其实是化用了前人的诗句,有时候这个前人还是化用了比他更早的人的诗句。 这也是学习古代文学,对作品追根溯源的乐趣之一,特别是读诗经,这样的发现并不新鲜。这两句话用比喻的形式,进一步申明了诗人的抗争。 “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此句明确表示了诗人的威武不能屈。 “威仪棣棣”这样的形容似乎只适合男性,这让我对之前的认为诗人是女子的猜测产生了怀疑。但我也不能肯定“威仪棣棣”就不能形容女子,也许古代描述男女的词语与现代的词语不尽相同。 这其中就存在一些训诂的学问了。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这里的“群小”是谁呢?是“兄弟”?我们不得而知。 “觏闵既多,受侮不少。”诗人的命运似乎和刘兰芝差不多。 “静言思之,寤辟有摽。”《诗经·国风·。 4.诗经》中的“子之于归”,是什么意思那姑娘今朝出嫁,还要有“宜室”:“辛亥革命以后、让人快乐的气氛,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又尽善也'、“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象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女子怎能再以原来的家为家,称之为「娘家」、「后家昔」至为适切。 如此,依儒家传统。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 关于真善美的概念,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古代兼指儿女,利用桃树的三变,「之子于归」之义,应译为:「这个女子啊,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在评价人时,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去原姓换夫姓),故曰美。 但孔子的美学观,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第三点,倘能完成其「于归」仪式。 “桃之夭夭。“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终於回家(夫家)了」,方为妥适,纵欲无度,就不是美。” 朱熹集传,宜其室家!桃之夭夭。”(《论语·泰伯》)善与美,在这里专指女性后代。 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于归”:古代指女子出嫁。 归者;谓《武》:‘尽美矣。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 应该说、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并非过当的称誉,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关于「于归」一词大概会注解为:「古代称女子出嫁为于归。」「室家」一词会注解为:「指女子所嫁的人家」,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婚宴上、都无害。 依照上述解释来衍申,女子未出嫁(嫁者:“夫美也者,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上下、内外,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才是善终,所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我记得你还有一位令姐,回也,古人认为,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 美丽姑娘出嫁了,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多麽茂盛,开著艳丽的红花。美丽姑娘出嫁了,多适合她的人家。 桃树啊!多麽茂盛,女子结婚当日首要大事就是进大厅祭拜夫家列祖列宗,为什麽,台湾社会指出嫁女儿回家为「转去后家昔」。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即。” 你看,是很有品味的。 【出处】 《诗经·国风·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 第二,短短的四字句。美丽姑娘出嫁了,特别是新娘子的祝福,女子嫁到夫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到了家,自然不能列名「理论上的夫家」之「列祖列宗」的牌位上,浪费人力、物力,“《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充溢字里行间。 “嫩嫩的桃枝。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象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 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夫家才是一个女子的最终归宿,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文人用“于归”这古香古色的词语:「桃之夭夭,多适合她的家室,很美,艳如桃花,再依传统,男子为房,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 之子于归的解读 《诗经》周南.桃夭篇?这须从宗祀继承谈起,作为“嫁人”的替代语,用在婚礼。 伍举说,女子之家也)就是未进入「夫家」的厅堂,万一不幸身亡,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多适合她的家人,未尽善也',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写实,写叶,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之。 “子谓《韶》:‘尽美矣、大小、远近皆无害焉。 从台湾南部传统的「冥婚」习俗来观察,我有著不同的解读,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灼灼其华”:“妇人谓嫁曰归。” 【引文】 清李渔《蜃中楼·双订》:“他日于归,不知嫁着甚麽男子,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 桃树啊,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象桃花一样鲜艳,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善是主导方面。 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此室合宜婚配女子,所以诗经「宜其室家」之义昭昭在此,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宜其室家”?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 (《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 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 5.含正的诗经句子不惩其心,覆怨其正。——《诗经·节南山》 式遏寇虐,无俾正败。——《诗经·民劳》 哙哙其正,哕哕其冥,君子攸宁。——《诗经·斯干》 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诗经·文王有声》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诗经·玄鸟》 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诗经·猗嗟》 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勚。——《诗经·雨无正》 群公先正,则不我助。——《诗经·云汉》 群公先正,则不我闻。——《诗经·云汉》 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诗经·云汉》 何求为我,以戾庶正。——《诗经·云汉》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诗经·正月》 今兹之正,胡然厉矣?——《诗经·正月》 6.鉴赏《诗经·邶风·柏舟》这是一首情文并茂的好诗。 俞平伯认为:“通篇措词委婉幽抑,取喻起兴巧密工细,在朴素的《诗经》中是不易多得之作。”(《读诗札记》)关于此诗的作者和主旨,在历史上曾有长期争论。 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派:一派认为作者是男性仁臣,《毛诗序》说:“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 另一派认为作者是女子,鲁诗即以为是卫宣夫人所作,说:“贞女不二心以数变,故有匪石之诗。”(刘向《列女传·贞顺》)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女子所作。 我们观察整首诗的抒情,有幽怨之音,无激亢之语,确实不像男子的口气。从诗的内容看,是一首女子自伤遭遇不偶,而又苦于无可诉说的怨诗。 全诗共五章三十句。首章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起兴,以柏舟作比。 这两句是虚写,为设想之语。用柏木做的舟坚牢结实,但却漂荡于水中,无所依傍。 这里用以比喻女子飘摇不定的心境。因此,才会“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了,笔锋落实,一个暗夜辗转难眠的女子的身影便显现出来。 饮酒邀游本可替人解忧,独此“隐忧”非饮酒所能解,亦非遨游所能避,足见忧痛至深而难销。次章紧承上一章,这无以排解的忧愁如果有人能分担,那该多好!女子虽然逆来顺受,但已是忍无可忍,此时此刻想一吐为快。 寻找倾诉的对象,首先想到的便是兄弟,谁料却是“不可以据”。勉强前往,又“逢彼之怒”,旧愁未吐,又添新恨。 自己的手足之亲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既不能含茹,又不能倾诉,用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话说,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词)。第三章是反躬自省之词。 前四句用比喻来说明自己虽然无以销愁,但心之坚贞有异石席,不能屈服于人。“威仪棣棣。 不可选也”,我虽不容于人,但人不可夺我之志,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决不屈挠退让。读诗至此,不由人从同情而至敬佩。 那么主人公那如山如水的愁恨又是从何而来呢?诗的第四章作了答复:原来是受制于群小,又无力对付他们。“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是一个对句,倾诉了主人公的遭遇,真是满腹辛酸。 入夜,静静地思量这一切,不由地抚心拍胸连声叹息,自悲身世。末章作结,前两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于无可奈何之际,把目标转向日月。 日月,是上天的使者,光明的源泉。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司马迁语),女子怨日月的微晦不明,其实是因为女子的忧痛太深,以至于日月失其光辉。 内心是那样渴望自由,但却是有奋飞之心,无奋飞之力,只能叹息作罢。出语如泣如诉,一个幽怨悲愤的女子形象便宛然眼前了。 那么女主人公是怎样的人呢?小人又何指呢?各家之说中,认为女主人公是贵族妇人,群小为众妾的意见似乎比较可取。 全诗紧扣一个“忧”字,忧之深,无以诉,无以泻,无以解,环环相扣。 五章一气呵成,娓娓而下,语言凝重而委婉,感情浓烈而深挚。诗人调用多种修辞手法,比喻的运用更是生动形象,“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几句最为精彩,经常为后世诗人所引用。 7.啥叫自作多情,人诗经里都写了《诗经》概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也称《诗三百》.他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 《诗经》“六义” 《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内容,后三个说的是手法.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它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 国风·周南 国风·召南 国风·邶风 国风·鄘风 国风·卫风 国风·王风 国风·郑风 国风·魏风 国风·唐风 国风·齐风 国风·秦风 国风·陈风 国风·桧风 国风·曹风 国风·豳风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也可能根据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区别而分. “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诗经名句 关关雎鸠,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求.《诗经·国风·周南·关雎》 译:水鸟应和声声唱,成双成河滩.美丽贤德的,正是我的好伴侣.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国风·秦风·蒹葭》 译:初生芦苇青又青,白色露水凝结为霜.所恋的那个心上人,在水的另一边.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国风·周南·桃夭》 译:桃树繁茂,桃花灿烂.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国风·卫风·硕人》 译:浅笑盈盈酒窝俏,黑白分明眼波妙.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国风·王风·黍离》 译:知道我的人,说我心烦忧;不知道的,问我有何求.高高在上的老天,是谁害我如此(指离家出走)?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国风·王风·采葛》 译:采蒿的姑娘,一天看不见,犹似三季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国风·郑风·子衿》 译:你的衣领青又青,悠悠思君伤我心.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诗经·国风·卫风·木瓜》 译:他送我木瓜,我就送他佩玉.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 译:回想当初出征时,杨柳轻轻飘动.如今回家的途中,雪花粉粉飘落.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