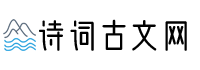
1.《诗经》对后世文学有哪些深远的影响影响 传统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 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 ,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 ,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 《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域外影响 《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26] ,确证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 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这证明《诗经》从丝绸之路外传历史相当悠久。[27] 中国与印支半岛和印巴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始于汉代。 汉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汉朝的教化,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必然进入。在古代漫长的交往中,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有通晓汉学的人士。 在越南据史书记载:李朝十世以《诗经》为科试内容,黎朝十二世科试以《小雅·青蝇》句为题,士人无不熟诵《诗经》。从12世纪开始出现古越南文学多种译本,越南诗文、文学故事中广泛引用《诗经》诗句和典故,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某些成语并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五经传入朝鲜。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丽三国分立,据《南史》记载,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28] 。 新罗王朝于765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一。高丽王朝于958年实行科举制,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 讲学《诗经》在朝鲜形成几个世纪的风气。到16世纪,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经学,现仍保存着他的《诗》说,《诗》说全面贯彻了孔子的诗教思想[29] 。 18世纪初编纂出版的朝鲜第一部时调集《青丘永言》,开拓了朝鲜近代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孔子编订《诗经》的思想和经验[30] 。韩国67所大学中文系讲授《诗经》,其中34所专门开设了必修或选修的《诗经研究》课程。 [31] 唐代日本遣。 2.诗经研究的意义在我看来《诗经》研究的意义可以这样来讲: 首先从诗经学上来讲。诗经学即研究《诗经》的学科。由于原始文献成书很早,所以后人不断层累完成的著作可谓卷帙浩繁。慢慢形成了体系极为庞大的学科,其中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是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未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被发现出来,比如他的作者与创作地点、时代,甚至于其作诗之义都存在着各种观点与争议。并且研究成果也由于视野不宽、材料有限有许多的讹误。现在的研究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旧的史料,或是根据近些年发现的新的证据,修正前人错误的观点、提出更为贴切的看法、甚至于是提出铁证将问题解决。 其次是作为其他学科的研究。 1.作为纯文学上的,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他的韵读、用字方式都可以作为当时时代语言用法的代表;研究他的这些创作特点也可以与楚辞甚至是《老子》等同时代成书的文献进行对比。 2.同时由于先秦时期文献很少,而诗经之中又记载着许多方面的诸如礼制、历史等的内容,可以作为研究先秦时代许多制度与史实、考古的重要资料;有诸如风俗、名物又可研究当时的风俗制度,各种名物诸如服饰,车马等。 3.同时,《诗经》作为十三经之一,也是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总的可以说其中包含的内容特别的多,极有研究价值,这里只是简单的概述之。 3.关于诗经的论文,1000至2000字左右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 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 《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 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 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 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 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 “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 《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 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 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 《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 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 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 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 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 4.关于诗经研究的毕业论文选题两千年来,论诗者多矣。 各个方面皆论述颇深。重复老调子,只是拾人牙慧而已。 我建议你讨论一下诗经与原始风俗问题,用人类学、风俗学、社会学眼光来解读诗经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那代人开始的,相对其他话题比较新颖,涉及跨学科问题,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建议你先读一读闻一多《诗经》类著作,如《匡斋尺度》、《诗经通义》甲乙、《诗经新义》,或许能有所启发。 后人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也不少,翻出几本典范,来读一读,看看除此之外能不能有新的视野和认识。只要有一点,一篇不错的论文就可以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