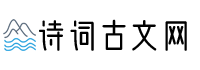
1.普罗诗歌的代表诗人是谁蒋光慈是这一诗派的代表。 蒋光慈自号侠生,“我所以自号‘侠生’,将来一定做个侠客杀尽这些贪官污吏”。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愤而想当和尚,改为“侠僧”,“我当和尚,也还是做个侠客杀人”。 在上海,蒋光慈进入共产国际开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随后就与**、**一起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2年,他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中共党员,第一次署名蒋光赤,以示倾向革命。 1924年,蒋光赤留苏三年后回国,即开始在文坛上大声疾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5年,他的诗集《新梦》发表,钱杏村对此评价道,“中国的最先的一部革命的诗集”,“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 而做下这一评论的钱杏村,当时是不到二十的少年,今天他的这一评语已成为文学史最常引证的结论。 蒋光赤的诗歌完全是诠释性的。 在他的诗中,愤青、小资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他写光明就全是美好的,新鲜的。“鲜艳的红花,娇滴的绿柳。” (《梦中的疑境》)红军士兵“放下枪头,拿起锄头;从枪头上得了自由,从锄头上要栽培这自由”。(《一个从红军退伍归农的兵士》) 比起诗歌来,他的小说创作艺术性更差。 他提供大众文学,却有着无可救药的小资情调。属于穷作家的穷讲究,用时人的评论,是“喝‘上海咖啡’而提倡大众文学”。 他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 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 瞿秋白感叹:“这个人太没有天才。” 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剧变激烈的社会,两三年之间,蒋光慈就时来运转。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普罗文学占据了文坛主流。蒋光慈于1929年东渡日本治疗肺病时写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仅在出版当年,就重版了六次。 书店老板为着赚钱,也常改头换面再版蒋光慈的旧作。例如,将《少年漂泊者》改为《一封长信》,《鸭绿江上》改为《李孟汉与云姑》等。 这跟当代的出版状况仍然相似,历史经常在这些细节上重复,虽然拙劣,但管用。 中国社会乃是风教之国,社会大众并没有多少定力,没有足够的认知能力,总是受时代氛围影响。 大革命失败后的挫败感,一旦主导了年轻人的心智,那种宣泄性作品就成为读者的安慰。 蒋光慈像一个笨拙的江湖医生,误打误撞地撞开了当时中国青年们的心扉,革命、爱情、理想等成为他小说中的主要元素。 1930年5月,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被当局查禁,他的肺病同时也恶化了。他搬到上海法租界里养病。 每天早上,他喝完美国房东派给的牛奶、可可茶、奶油汤后就一个人去法国公园,边散步、边继续构思《咆哮的土地》的后半部分。 但组织却需要他做出贡献,需要他提供开会的场所。 1930年秋,蒋光慈反对在他的住处开会,并强调“一个屋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一开会就开倒了……”过了几天,左联党组的负责人就对蒋光慈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去暴动!”蒋光慈为此递交了“退党书”。 10月20日,《红旗日报》发表了“蒋光慈是反革命,被开除党籍”的消息。 除了其不愿服从纪律、参加组织生活之外,其中一项指责就是他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过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他虽已被开除,但仍有创作激情,1930年11月,他的小说《咆哮的土地》脱稿。 这是蒋光慈最后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在艺术成就上屡遭蔑视与非难之后,文学史上获得评价最高的一部作品。 正当人们对他的前途充满乐观估计时,《咆哮的土地》遭到查封。 蒋的作品被查禁后,生活变得日益拮据起来。蒋光慈不仅有肺病,在医院里,还查出了肠结核。 在当时,肠结核是一种绝症。 这个无根的革命文学青年,赤条条地来去。 他死于1931年,年仅30岁。他跟任何大的政治、文学势力无关,只是拙朴地表达了个人的经验感受。 同年9月15日,上海出版的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专门出了一期“追悼号”,哀悼蒋光慈等同志不幸逝世。钱杏以方英的笔名在“追悼号”上发表的一篇悼念蒋光慈的文章,指出:“他生活了三十年,在他的全部生命之中,他是以无限的精力献给了革命。” 著名作家郁达夫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沉痛地指出:“他的早死,终究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损失”。 建国以后,党和人民给予蒋光慈崇高的评价。 1953年,纪念蒋光慈逝世22周年前夕,上海市文联经过多方追寻,终于找到蒋光慈的遗骸,并正式迁葬上海虹桥公墓。 尽管蒋光慈自参加革命之后从未回过家乡,但是大别山的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个为革命文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儿子。 1957年2月,安徽省六安县人民委员会决定追认蒋光慈为革命烈士。 扩展资料 诗歌理念 受国际文艺思潮(苏联“拉普”、日本“纳普”)的影响 1、普罗诗派把诗歌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无限夸大文学的政治宣传作用。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用辩证法方法写出生活的出路,促进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否则就是虚无主主创作。” 《俄罗期文学》称赞俄无产阶级诗人“把诗做为红军的大炮,应时势需求” 钱杏顿《幻灭动摇的时代推动论》“文学于宣传的关联是必然的,无论哪一阶级的文学作家都是替他们自己的阶级宣传。 |